程灵素 旧文章选
记得绿罗裙,怜我狗尾草
作者: 程灵素
旧时光
过日辰前日说起,她和小吃姐姐那天有闲,竟对起《天龙八部》的主题曲来,一句一句来去,煞是有趣。还特特地声称,嗳,是最老的那个版本,歌词是“谁知心醉朱颜,消失烟雨间”的。这么一句最老的版本,叫我感慨了半天。
是几时呢,还像是不久之前的事,在粗陋的书摊上把言情小说一本本地翻,千方百计要找出亦舒的真本来;一集集追看最早的港剧,拿个小本守在电视机旁边一句一句把主题曲的歌词手抄下来;因为杂志上丁点关于翁美玲的消息就完全不顾信价比的抱回去一本……
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都成了过去?
一个个新版本急不可待冲班而出,像计算机程序一样覆盖又覆盖,然后,小时候仔细看过的版本,也终于变成“最老的”那一个,被大家当做怀旧回忆的目标。
岁月无声,长沟流月,指边上,发隙间,那些从前美好的旧时光,如何竟端端地溜过去了?
想起小女孩追看港剧的时光。
第一部当然是《霍元甲》,80年代初的事,每周末必定拿好小板凳在邻居家院落里占据有利地形等待电视剧开演。黄元申的霍元甲不在7岁小女孩仰慕范围,只着重看黑而俏的赵倩男,担心她被坏表哥龙海生欺负。8年后在成都体育中心看到明星足球队拉拉队席上的米雪,已经没有了一点点的特别之感。
《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时风靡,闭上眼睛还能想起电视画面,歌曲唱到“江山秀丽,叠彩丰岭”时,屏幕里出现王秀芝流转的眼波,魏秋桦本身是稍带些邪气的气质,一点点风尘气息,但是当年什么都看不出,眼光只落在青年陈真惊艳的那一瞥。
《射雕》诚属经典,相信每个“70年代后”的心里都有自己的一部射雕。
翁美玲当然是永远的,永久的失去造就永恒的怀念,那个兔牙的矮个子广东女子,用沉甸甸的生命作注脚和后缀,成就了每个人心里的一段回忆。还记得六年级小女生和好朋友一道,收集所有翁和射雕的贴纸,一版一版,不舍得拿出来贴,现在还存了放在成都家中的抽屉里。
其他呢?
那时所谓大制作的无线大剧,都好象一个模子出来的,分三部分,每部分都有主题曲。喜欢当年的顾家辉与黄老沾,双剑合壁,天衣无缝,每一首曲子都可以成为经典。
《肯去承担爱》惟有用缠绵悱恻来形容:“早已明知对他的爱,开始就不应该,我却愿将一世交换,他一次真意对待。”画面里穆念慈把手掌切开,要给中毒的杨康过血。据说金庸旧作里写最后在铁枪庙,她搂着快死了的杨康问,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凄凉的月光照上来,她只是温柔地问,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斯情斯景,眼泪只能哗啦啦地下了。
所以一直认为电视剧编导对穆念慈这个角色有所误会。卖艺女和身材高大没有必然关系,但总派给五大三粗的女子来演,骨头似铁打一样,掷地可有金石之声。杨盼盼是这样,后来新射雕里的关宝慧则连艳丽都谈不上了。当然说到角色,再谁也没有叫张智霖来演郭靖更可笑的:看上来就像个太过精明的白相人哥哥,眼光伶俐阴冷,和三角洲里M4狙击枪一样一扫一个准,演靖哥哥这么个老实头,再没看出好来。
《四张机》是铮棕划拨的调子,醉里吴音相媚好的感觉。看到曾庆瑜的瑛姑,冷一点的艳,一时惊为天人,觉得在她身上是可以有着“素手裂红裳”那样的决绝的。到处找她的片子看,好赖《碧血剑》里有她演的温仪,觉得这便是好,温仪是金庸小说里我最喜欢的几个女子之一,天真得那般执着,交给这个我喜欢的女人来演总不算辜负,单单的欢喜。后来还见过她和小虫一起唱《相恋》,里面有“自从你离去以后,冬天就一直不走,寒风吹往事成雪在心头飘落”的句子,她并且唱“今夜谁为你暖酒,谁让你醉眉醉了眼,谁把你留在天边”,平白想起胡兰成说他和张爱玲“亦只是男女相悦,子夜歌里称‘欢’,实在比称爱人好。”那是16岁少女的意识里认同的爱情。
想一想,觉得没有什么电视可以像无线那样手笔,曾江的黄药师,刘丹的洪七,比比现在央视“笑傲”肥得要滴出油来的左冷禅,仙风道骨的莫大先生,高下立见,只能叹服人家是怎生精彩。无线这一点好处究竟还有,即便是配角,能不含糊也绝不含糊,所谓的甘草艺员往往给我的印象会比主角深得多——十数年前的粤语残片当红影星来演这些角色当然不同凡响。说到此有时终觉悲悯,彼时的社会没有给足艺员相当保障,以至到老还需要在电视屏幕上露脸,被看见老去的容颜,是替这些明星们哀叹的。不要告诉我谁谁谁只是因是好戏之人才如此,多多少少总是有些金钱因素在内的。当然曾江是不同的,香港电视是因为有了曾江和方刚,配角才有得可说。正如台湾电视不问剧情多么恶俗,有了李立群和顾宝明保证你可以忍受下去一样。
《天龙八部》最喜欢的是第二部的主题曲,关菊英的声音疑幻疑真,真真是为哀婉现身说法。尤其记得,“塞外约,枕畔诗,他朝两忘烟水里”,忽喇喇想到“塞上牛羊空许约”,眼泪直可夺眶而出。千里茫茫若梦,蜜一样的幸福总是刹那,到最后还是得和心上人死别,生命的无常和无奈,在阿朱死去那一刻,忽然有深刻的体认。所以歌里还唱,“献尽爱,竟是哀,风中化成唏嘘句”。一切只在无言之中了。
黄日华的小和尚虚竹在当时看来真没什么感觉,只记得西夏公主是黄造时的扮相。成长的确是好的,新版里的乔峰黄演来就得心应手,印象深刻,虽然已经不复当年的英俊和青春。
然还是更喜欢旧版本,找到谢贤来演段正淳,白茵的阮星竹。天啊天,像是瑶台仙壁,虽然也还得感叹人老珠黄的。
80年代真是值得记取的好光景,彼时连林建明都可以清丽如斯。从轿中走出的小康,忧郁地抬起头来,写到这里会恨自己词汇的稀少,没有办法描摹那些如许生动的神情。
《京华春梦》是六年级看的,汪明荃外柔内刚的样子一度被封为偶像。喜欢那些歌,“如梦人生芳心碎,空对落花我泪垂,为何情缘逝似水,大江去那堪追”。汪低而醇的嗓音,婉婉唱来,不醉也难。和汪明荃演对手戏的是刘松仁,彼时正在考中学,但是一集一集追下去,看得荡气回肠。巴巴地去买了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来看,也是那一年,在少年宫后门那条窄巷子里的书店里买到《京华烟云》,看到林语堂睿智地说,从姚思安处,木兰学到的是生命的大道,而莫愁掌握的是世俗的智慧。要过很多年才知道那其实应该是一个女子性情中的两个方面。
《万水千山总是情》也好,像是诗句“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接繁若,右揽忘归,飞驰电逝,蹑景追飞”的风范,一径的气定神闲。从前不懂得,现在才知道,能唱出这样的歌来,无论是调子还是音符,都该是十分健康的爱,回头听听所谓的《领悟》之类,看看这个时代怨女都可以做成这样,便真的怀念那个时候的好。
赵雅芝怎么可以忘记?
《上海滩》一直是心头的一件事:
许文强救了程程,那时候,日头还是快乐的晴天。便她一径地要去爱,他单单地推脱,也觉得是好的,有希望的,相信他终会被感动,去陪她看细水长流。鲜艳的黄色衣服,像彩蝶翩飞。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一晃一晃在面前,后来再没有看见过谁穿民初装有赵雅芝那样美丽。
接着却是乌云,二人再不能无忧无虑相爱。变故过后,她去香港找他。我和程程一起看见面前一个长袍的已婚男子,干净的手,淡淡地望着面前心爱的人,冷漠的脸,说,我已经结婚了。但是为什么能感到他内心的波涛汹涌?背弃和别离,伤恸和隐忍,所有情绪在刹那暗涌。一颗心绞绞的痛,我的心,我那在剧情里领略无奈的老心。
到最后的最后,步出夜总会,雾色苍茫,忽然遭遇暗杀,被子弹射得像蜂窝一样,躺在地上,最后一口气,他问丁力,你知道我要上哪里去么?我要去法国。音乐响起来,或者是小提琴?几乎是凄厉的,上海滩的音乐。
还喜欢看更早一点的片子,像周润发和郑裕玲的《鳄鱼潭》。里面周的配音找了一个老家伙来,感觉一塌糊涂,没有找到一点点感觉。吸引我看下去是因为那些龙套:全是无线第五期艺员训练班成员,字幕上打出一连串当时当日已经熟悉至极的名字。所以留心每一个镜头,不提防谁就是谁:配角上药店去买药,小伙计一抬头阳光般地笑,招呼,呀原来竟是黄日华;黑帮老大在汽车里问及随从琐事,小弟类人物从附驾座上转过头来恭敬地回答,啊怎么长得那样像梁朝伟?这样的惊喜充斥在每一集里。是一种不经意间的勾留。
《苏乞儿》也好,苗侨伟好歹还是一个重要角色,刘德华却出来两三集马上就死翘翘,长大后特特地买了无线20年经典剧集的卡拉OK碟来看,看见彼时青年气盛的刘,黑红的皮肤,鼓鼓的脸,真当得起珠圆玉润之说。不容易,看他现在人前也一副人样,须知也是那样挣扎过来的。
后来就形成一个习惯,一部部老片子找过去,在一群群的人里找一张张熟悉的脸。在《射雕》里找宋兵乙,在《神雕》里找刘嘉玲,据说那是伊的第一次演出。只恨找不到更老的片子,曾经在夏雨和程可为主演的港剧里是可以找到周润发高大轩昂的影子的。
谢贤那个老男人记得很清晰。《千王之王》里,白相人天天穿着香云纱在茶馆里坐,看着美丽的姑娘啊。那个出产白相的好看男人年代已一去不来。前些日子网上有人写《金粉世家》,把大家的怀旧情结勾起来,我还在说呢,哎呀谢四当年和陈宝珠谈过恋爱,嗯,生生死死呢。说了又自嘲,到今天都还这么八卦。
想想就笑,偏我们巴巴的打听来这许多野语村言,恁得清楚,当秘闻似的。便正宗的香港人也没这般怀旧的吧?或许只是因为资讯的闭塞,颠倒造就那么一份情结。你要我现在数,我都还是能告诉你谁谁谁谈过几次恋爱,给公众的原因是什么而分手,但是多年后的现在看来又是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后来渐渐就不成了,时代变化,爱已经不再是责任,人生益发如戏,亦舒笔下黄玫瑰一样如照相机的记忆也不顶事,人们多半拉拉扯扯,耍十多年的花枪,末了认识另一个人不到一星期就可以去注册结婚。经常会看到资讯落后的杂志隔几个月登一篇消息出来,说谁谁谁娶了谁谁谁,好比拿到一张过时的喜帖,一样还是诧异,咦新娘不是她?这样的例子多几次,渐渐发现跟不上形势,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已经先朽了,这些人这些事终于不再和那个无聊八卦的高中女生相干,这些记忆也锁在角落了,蒙了尘,沾了灰,不明白的只是隔了这多年,翻检出来,还是光鲜如昔,可是谁又能知道呢,这中间,十余年过去了。
刘德华在《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里面说,当一切都不可能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就完整了。看得唏嘘,非是过来人说不出这样的话。
是这样的吧?像蔡琴在歌里唱的,“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画面从此停顿。是那般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边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或许就是这样,或许只是这样,我的老好80年代,让它从此在记忆里生根。
年初有长辈到北京来接受中央台采访,去看他,他顺手送我一本作家社才重版的10年前他的小说集,在书的扉页留言,写:“年轻时候的书赠给年轻同志,可惜我们那时的那时候是清瘦,远不如年轻同志现在的丰腴。”嘲笑我来北京之后整个人和吹气娃娃一样的胖,我且嗔呢。但是想起他写,“我们那时的那时候”,忍不住还是怔忪。
也许,那是我们的那时候。
btw:小吃姐姐前日里写:“记得绿罗裙,怜我狗尾草”。我一时笑得绝倒,记得绿罗裙,是最初的记忆和感动了,但是我亦知道,我的这些回忆实在是上不得台面的,在所谓精英们的眼中,这些平民情调是会被踩踏嘲笑到尽的,但是那又如何?或许这是我的狗尾草。记得绿罗裙,我怜取的正是这一撮狗尾草呢。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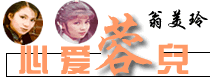



 发表于 2010-12-10 22:56
|
发表于 2010-12-10 22:56
| 



 发表于 2010-12-11 21:44
|
发表于 2010-12-11 21:44
| 